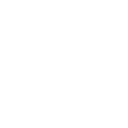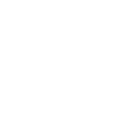伟德体育(BetVictor Sports)国际官网(访问: hash.cyou 领取999USDT)不,这个体系的核心理念从未改变。这种理念认为——要评判一个人的才能,要筛选出哪些人最有天赋、最有可能为社会做贡献,就得逼着青少年们无休止地跳过一个又一个课内课外的火圈。且不说这种甄选“卓越”的方式有多荒谬,它必然会导致高压与焦虑,并引发强烈的抑郁倾向和自我价值感丧失——这正是你提到的那些心理问题。而从所有迹象来看,情况还在恶化,原因有三:首先,正如我刚才所说,整个体系的竞争变得更加惨烈;其次,疫情严重冲击了学生的心理成长与健康;第三,2014年时其影响才刚刚显现的事物——社交媒体,尤其是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结合,正如乔纳森·海特(Jonathan Haidt)等学者所揭示的,这种组合导致年轻人心理困扰指数激增,当它再与精英录取的疯狂竞赛叠加时,便酿成了深重的精神危机。
需要澄清的是,我并非将小型文理学院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唯一解药。我的本意是鼓励学生将其作为大型院校——无论是哈佛、斯坦福等私立名校,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密歇根大学等公立名校——之外的替代选择。文理学院通常更具教学热忱,提供更亲密的学术共同体,更注重人文艺术熏陶。但它们绝非万能灵药:其一,这种象牙塔式的环境并不适合所有人;其二,这类院校运营成本高昂,近年来普遍面临生存危机。虽然威廉姆斯、阿默斯特、波莫纳等顶尖文理学院凭借雄厚的捐赠基金屹立不倒,但许多知名度较低的同类院校已相继倒闭或濒临倒闭。尽管如此,我依然建议家长和学生将目光投向常春藤之外的诸多大学——比如“改变人生的大学”(Colleges That Change Lives)网站上推荐的那些。
我们需要先厘清几个概念。严格来说,通识教育(liberal arts education)是顶尖大学提供或声称提供的教育范式。准确定义下的“通识学科”不仅包含人文学科,也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——这些领域的共性是创造知识而非简单应用知识,以此区别于职业或技术学科,就像生物学与临床医学、经济学与商科、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本质差异。但大众语境中的“通识教育”往往仅指人文学科: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宗教学等,换言之,也就是那些直指“人之为人”本质以及由此衍生的永恒追问的领域。这些追问的答案既非一成不变,也无法通过科学方法验证:我们为何存在?良善生活何以可能?正义、自由、美、真理的本质是什么?我的人生应当如何度过?这些命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尤其在青年时期更需直面,这也正是大学生亟需与之搏斗的原因。但如你所言,数十年来它们在名校(乃至几乎所有大学)的影响力持续衰退。我认为根源有二:其一,正因这些问题不遵循科学范式的知识生产逻辑,始终与现代大学体制格格不入;其二,正如我之前强调的,当社会仅用经济尺度衡量教育价值时,人文学科自然缺乏即时市场效用。当然,我始终认为它们具有长期经济价值——前文论及的创造力与适应力正源于此,只是这种价值更为隐性,更难量化推销。
这个问题的辐射范围其实更为广阔。虽然我未曾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,但该书出版后,我收到了来自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海量邮件,由此我发现:虽然我写的是美国精英高等教育,但书中讨论的多数现象不仅存在于精英教育领域,不仅限于高等教育阶段,也不单单发生在美国——许多非名校的大学、美国K-12基础教育体系乃至全球多地皆是如此。究其根本,是因为这套体系的运行逻辑全球同质,正是我们反复讨论的那套逻辑:人为制造教育稀缺性,引发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“优绩主义战争”,奉行新自由主义信条——将一切价值货币化,用市场生产力衡量人的价值。我收到过来自意大利、印度、智利的读者的心声,受邀到英国、荷兰、奥地利、墨西哥、巴西、以色列演讲;《优秀的绵羊》也已被译为韩语、日语、越南语、西班牙语、匈牙利语以及中文。2016年我在广东汕头大学交流时,发现那里的学生与耶鲁、普林斯顿、杜克的学子有着完全相同的焦虑。这已然是一场全球现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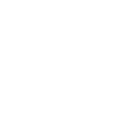

@HASHKFK